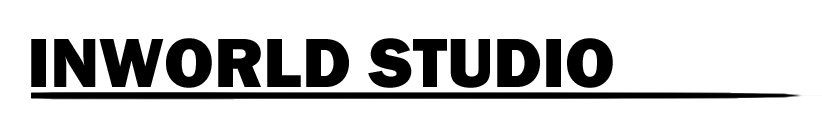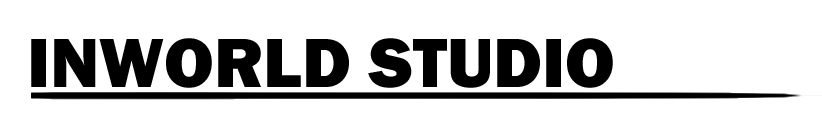创业初心
不知道你是否曾为这三个问题所困扰过:
- 我为什么选择设计游戏?
- 如果衣食无忧,我想设计什么游戏?
- 怎样才能设计一个好游戏?
这么多年我们游戏行业一直在研究“怎么赚钱”,却很少有人出于社会价值告诉我们:还可以设计些什么,也更少有人直面自己的内心:现在的我为什么设计游戏?
通过这封信,我想向你分享:
- 我为什么想设计游戏
- 我想设计什么游戏
起点
我从12岁就决定要成为一名游戏设计师,但是到16岁时却遇到了灵魂拷问,开始困惑自己人生的意义,困惑我和世界的关系,困惑我未来努力的价值——那是游戏被称作电子鸦片的年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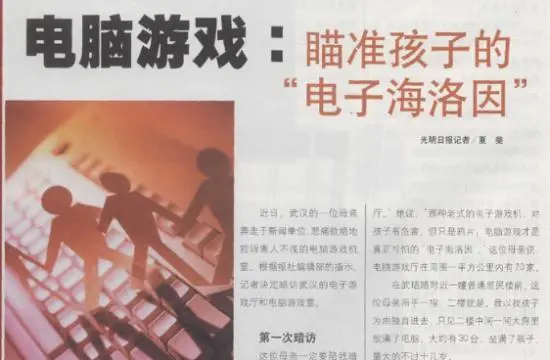
曾经参加一场青年空间活动,Host提了一个问题:如果有两个选择
A:我能获得10亿现金,但是我以后不能工作、投资、创业,这些钱只能用在我的个人消费上
B:我能获得500W现金,但是只能用在文学、艺术、影视、游戏创作上,不能用于个人消费
你会怎么选?
2010年的我,也许会选择A。因为那时我虽然已经立志做游戏,但是对于游戏的态度是一种兴趣热爱。我还不确定,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。 2010~2013年是我人生中最低谷的三年,在那三年中,我经历了家庭的彻底破碎,感情的爱而不得,人际关系的危机,身体的顽疾,理想的反复动摇。几乎每隔一个月,就会有一个声音过来严肃地问我:你的一生真的想做游戏吗?游戏,有什么意义吗?
这质问就像一个严厉的师傅,惩罚他最难管教的徒弟,用棍子把他打倒,等他刚刚站起来,摇摇欲坠,又一棍打倒。站起来,又打倒。站起来,又打倒。反反复复三年。 痛苦,会让人寻求解脱。要不然解决痛苦的根源,要不然解决痛苦的感受器。而我在长时间与痛苦相处之后,让我能够近距离观察它,它的形状,它的味道,它的运作原理。解决不了它,那我可以试试解构它。这个过程,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:
我所体验着的痛苦,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也正在体验,我能不能为此做点什么——用我最喜欢的方式。
信念
带着问题,我从Jane McGonigal的《游戏改变世界》中找到了启发。她认为对许多人来说现实是“破碎”的,人们很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成就感、自主感、目标感和社交连接,或成本很高。游戏通过设计精巧的挑战和激励机制,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情绪,让人们能够体验到这些需求的满足,从而帮助填补现实世界中的空缺。在游戏被喻为电子鸦片的年代,Jane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,让我能够重新审视游戏的价值和潜力,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社会。

在那同时我也从南怀瑾老先生的《金刚经说什么》里找到另一种人生定位。他介绍了佛教体系中罗汉的任职标准:罗汉,达到阿罗汉果位的修行者,断除了烦恼,摆脱了生死轮回的束缚,实现了个人的解脱。也介绍了菩萨的任职标准:菩萨,意为“觉者”,为了利益众生而发愿成佛的修行者,不仅追求个人的解脱,更致力于帮助众生脱离痛苦,为众生的福祉而修行。佛教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的解脱,而是众生的解脱。 我一看,菩萨境界高,我可以应聘菩萨吗,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文书菩萨,我,游戏菩萨,咳咳~

16岁,我开始思考游戏的力量,游戏的可能性,游戏能够给人们带来的积极影响。这些问题,就像穿刺过云层的光芒,让大地重新燃了起来。有一天师傅又想过来抽我,我反手就给他一击,缴了他手中的棍子,同时甩下一句:“从现在开始,请叫我:Game Bodhisattva。” (别试了,我知道你念不出来)

2016年,就开始忽悠后辈们把人生奉献给游戏事业了——啊游戏菩萨的本职工作
已经过去10年了,但是直到2023年的今天,我仍在持续思考人的痛苦、快乐、幸福、需求,以及游戏具体能为它们做些什么。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哲学,都在不同的维度提供思路,然而,却没有游戏学,把所有相关且有用的信息和方法论汇集成理论体系。但是至少有一件事现在的我非常确定:只要以世人的福祉为目的,游戏就有着巨大的积极的可能性。
如果“玩”能为人们带来积极的健康的快乐,游戏就有意义,我们这些游戏开发者毕生的选择就有意义。
10亿现金,如果不能转换成社会价值,那它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。 2023年我会怎么选?我会选择:为给人们带来快乐设计游戏。
现实
当初带着这样的理想,第一次进入游戏公司的情景,第一次布置好自己的工位,跟左右的同桌打招呼时假装腼腆的样子,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心动。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你的职业生涯中,接到的第一个任务。我的任务是:学习使用SVN。到现在已经入行许多年,经历了几个不太成功的项目,也在行业内看到许多勉强、妥协和麻木。让我第一次印象深刻的冲击,是我在运营公司实习时,去和CP方开会。对方制作人穿着麻灰色的宽松牛仔裤,腰间吊着铁链子,38岁上下,扎了一头长发。他拍着桌边跟我方老板坦白:“直接说吧,想让我们抄哪个游戏,只要你说得出,我们就做得出!” 我当时喝的水晃荡了两下,一方面是感概我方BOSS为何如此强大,另一方面感概,眼前的这个游戏制作人为何如此堕落。
在进入游戏大厂前,我曾经以为可以依靠大厂的平台和资源做出更伟大的作品。但是后来听闻了很多来自国内Top5同行的感概,我发现几乎每个手里提着西瓜刀的从业者都遇到过这两个问题:
- **许多项目决策者根本不玩游戏,**不懂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,却还要给我们做决策
- **创作意志难以统一,**大公司的决策层太多,每个领导都有权力,他们的意见都在指导项目方案,而他们自己往往也不一致
举个例子,有个深圳的制作人朋友,他的项目在公司内部要过评审才能继续开发。但是评审之前要先给上级领导点头。他得先通过领导A,A觉得可以了再给领导B,B觉得可以了再给领导C。

要是B觉得不行,他会连领导A一起骂。要是C觉得不行,他会连AB一起给脸色。但是领导A是一个讲究做游戏要原汁原味的领导,B是一个注重概念特色的领导,C是关心玩法循环设计的领导。更有趣的是,他们三,以及评审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,都没亲自玩过这类游戏超过10小时,对于这类游戏的乐趣从来没有亲自感受到过。如果这个项目是那制作人朋友从零创新也就算了,但这项目是他公司市场研究部通过数据调研,发现这大类方向有钱可赚,是领导C指派让他做的。他怎么才能把这项目做出来呢?
遇到意见不专业,意见不统一,如果项目是一个人,它八成就是个内耗的人。自己能出院都不错了,还搞啥给人带来快乐设计游戏呀,我们这些开发者都不快乐,怎么给人带来快乐?
后来我也亲眼看着一些意气风发的团队,从做正经游戏转型到抖音短视频追热钱。也有从小区里打拼出来的工作室,跟风做了几个当时火热的概念,最后跟着泡沫一起消失。也有坚持不接受资本投资,两三个人吃老本用几年做完一个独立游戏,最后却只卖出了几千份。也有因为不做团队管理,项目组拍宫斗电视剧,真正想做事的人被挤兑边缘化,德不配位的人占着关键位置混吃养老。也有大公司的头部产品,为了短期割到更多的韭菜,决策者明知道会牺牲品质和产品寿命,也选择割一波跑路(在厕所听到的,别细问)。
是谁,在为了给人们带来快乐设计游戏?
(腾讯:用心创造快乐?)

我曾深度参与过预算超两亿的项目,当我了解到高层决策者对此项目的期望是上线首季十亿流水时,我明白设计者的重任和压力,我也明白了**“快乐”并不是他们的目的——“快乐”只是他们的手段**。
我不接受这样的观念。我不止一次和人在厕所争吵:一个游戏,应该以创造精彩的体验为第一目的,还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。明确选择赚钱的好汉都被我按进了马桶里。还有一种声音,他们的解释:赚钱和体验并不冲突,而是相辅相成的。只要体验好了,就能赚钱。反过来,体验不好,也赚不到钱。这说法虽然无懈可击,但是回避了问题:做一个游戏项目,第一目的是什么?
我们为什么设计游戏,这是一个关注价值观的问题,当我们遇到最本质、最关键、最重大的决策时,影响我们判断的正是我们底层的价值观。一个作品所具有的灵魂(如果有的话),其中一部分也正是价值观的映射。
我主张的价值观:
- 做游戏的第一目的,是为人们带来快乐。
- 盈利很重要,但是盈利是我们实现愿景和使命的手段。
- 如果忘了初心,被盈利成了最终目的,那就别做游戏了。会害人的,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。

方向
为了给人们带来快乐,我们想设计什么呢?我们如何解读快乐呢?
我相信每一个有思想的设计师都会有自己的解读,而在我的游戏设计方法论中,我把**“快乐”约等于“价值”**。我的每个项目确立都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:这个作品将为玩家带来什么价值?

我自己作为一名玩家,最能触动我的是能够满足深度社交需求的游戏
- 让彼此不相识的玩家能够通过游戏产生互动,建立连接,从而产生关系,沉淀关系
- 让原本互相认识的玩家能通过游戏产生话题,共享经历,从而深化关系,提高连接质量
在十几年之前,我从早期的MMORPG中体验到了一部分社交需求的满足,但2010年之后MMORPG越来越套路化,让人感到厌倦。而短平快的MOBA游戏却又无法沉淀关系。世代交替之间,人们永恒的社交需求无处安放。
而那时刚刚兴起的生存沙盒游戏,却意料之外地在社交方面提供了更细腻的体验。
我第一次感受到“我要和大家一起活下来”是在《DayZ》里。我和两个队友饿得前胸贴后背,两眼发黑。我们沿着公路一路翻垃圾桶找吃的,恨不得把路边的丧尸也烤了吃了。路过Olsha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罐头,我让他们两先吃。他们一人一口,结果轮到我的时候罐头就空了。不过下一秒,那两个呆逼中毒死了。2012年。